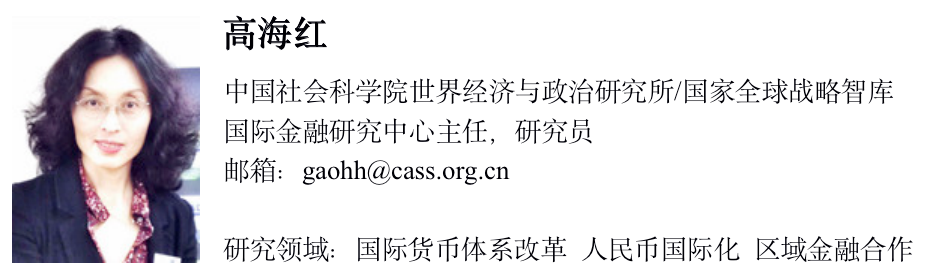
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货币政策既有对他国的溢出效应,也承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溢入效应,而后者对本国的经济政策目标形成了干扰。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享受美元储备地位带来的收益与其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这其中所形成的种种悖论,在单一货币成为主导储备货币的体系中会有所放大。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一直以来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纵观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历史,美元的国际货币角色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浮动汇率时期。尤其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在缺乏全球性汇兑制度安排的支持下,美元仍保持主导地位。这一事实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也带有自身的矛盾。在更多的关注集中在美元地位带来的所谓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同时,另一个事实往往被忽视,那就是作为主导货币美元也同样承受嚣张的负担(exorbitant burden)。成为储备货币,既有收益,也有成本,而后者对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方向更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1999年首次公布COFER季度数据至2021年第二季度,成员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平均为64.83%;欧元为22.46%;日元为4.37%;英镑为3.89%。从变动趋势看,美元占比有所下降;人民币于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官方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也开始公布,人民币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图1)。然而在长周期中,美元在过去70多年中的比重下降速度十分缓慢。为什么美元会长期保持主导地位?
储备货币地位的形成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并成为贸易逆差国;而美国迅速崛起,成为顺差国和贷款人,并因欧洲战争还款输入了大量的黄金。美联储也与1913年正式成立。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开始形成,并开始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一时期美元地位的崛起绝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进一步稳固了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设计上确立了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的法币与黄金挂钩,其它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当时重要的顺差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也获得了一票否决权。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因新兴市场力量的兴起发生了变化。然而由于多重因素影响,美元仍是世界各顺差国持有的主要储备资产。这其中对美元地位的识别缘于一系列既定的条件,比如: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这是美元具有的绝对优势;再比如,货币发行国的法治环境和体制的稳健性也是美国所能提供的相对优势。
美元地位缺乏替代性或存在“别无选择”(TINA)效应。TINA效应是美元地位的一个重要隐含条件。TINA 这一说法最初源自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福利国家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在为其自由竞争和放松管制的保守党施政纲领的辩护中也使用这一术语。美元TINA效应是指,在国际货币的选择中,由于缺乏其他可替代货币,美元作为主导货币是别无选择的结果。从二战后储备货币的发展历史看,行使部分储备货币职能的特别提款权尽管存在多年,但自身的局限性极大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其他包括欧元和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在历次金融动荡和危机发生时期,美元的避险功能仍显示其具有“别无选择”的优势。
储备货币地位维持具有网络外部性。这一网络外部性会通过转换成本和最低有效规模这两个渠道提高退出现有体系的成本,从而增加体系可延续的惯性。具体而言,美元计价能力存在自我强化机制。这表现为在企业、居民和银行部门之间为冲销汇率波动风险有足够的动机彼此相互使用美元。例如,企业使用美元计价,为冲销美元汇率风险,需要进行美元对冲交易;而银行为满足企业的需求也愿意提供美元贷款;同时,银行为了防止货币错配也需要吸收美元存款。这在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美元使用和持有的强化机制。从储备货币发行者的角度看,当全球对储备资产需求的增长快于发行者的偿债能力时,发行国事实上享有发行储备资产的安全溢价,这也构成了对储备货币持续过度发行的一种激励(Farhi and Maggiori 2017)。
在学界,针对美元体系的主流讨论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阵营:“哈佛观点”和“伯克利观点”(Eichengreen,2019)。哈佛观点以数据和实证研究为依据,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存在惯性,其主要表现为美元主导的货币计价范式(DCP)广泛存在。具体来看,美元充当第三方货币,其汇率变动对一国贸易(出口)所产生的影要大于贸易伙伴之间双边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Gopinath et al 2020)。这一研究还隐含这样的政策含义: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会通过美元汇率传递到以美元作为贸易计价国家的出口价格。
如果说哈佛观点倾向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伯克利观点则更倾向于多元体系的存在逻辑。基于对历史观察和总结,伯克利观点认为多元货币体系在历史上就存在过。比如,在金本位时期,尽管以黄金和英镑为主导,但德国马克、法郎等小币种也发挥储备货币职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镑和美元在全球流动资产和贸易计价和结算中也曾平分天下。简言之,在伯克利观点看来,多元货币体系是定律而不是个例。
“嚣张特权”这一概念首次由法国前经济部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65年提及,意指美国以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为其赤字融资的能力,并担心法国将因此遭受损失。随后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艾夫对美元嚣张的特权如何运转进行了具体阐释。
理论上,所谓嚣张特权表现在发行国可以凭借货币独特的储备地位以低成本向全球借债;发行国通过运行经常项目逆差获得自动保险;过度发行债务的情况下事实上获取安全溢价;发行国获取铸币税或以通胀方式进行债务货币化以减轻债务负担;在美元情形下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赋予美国以金融制裁达到其政治目的。
与上述收益相伴而生的是相应的成本。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货币政策既有对他国的溢出效应,也承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溢入效应,而后者对本国的经济政策目标形成了干扰。比如,美元地位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不断以低息向国外持有人发行国债。在不确定增大时期,寻求安全保护的外国投资者纷纷购入美债,支撑美元并以资本流入修补贸易逆差,帮助美国平衡收支。这实际上对美国提供了自动保险机制。然而,由于这一自动保险需要一个强势美元,而强势美元有损于美国的出口(Bergsten,2009)。从储蓄角度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需要吸纳全球顺差和储蓄来维系美元的储备地位,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是构成一种负担(Pettis,2011)。更进一步,尽管美元主导地位极大降低了美国企业国际交易的汇兑风险,也为美国政府以超低成本在全球融资提供了铸币税收益,但是由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在全球失衡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与经常项目差额常态水平比较,2019年美元储备地位对美国经常项目差额造成影响,除了包括合意政策、净金融资产、石油、人口、预期增长和制度等其他诸多因素外,美元高估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贡献率达到1.8%的水平(IMF,2020)。这样一种高估与逆差的组合,在事实上构成储备货币在收支调解中所承担的成本,因为汇率持续高估对外部收支调节造成扭曲的同时,也对国内就业和增长具有抑制性作用。
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单一货币发行国需要维持独一无二的偿债责任。这里的前提是不得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债务货币化,因为只要能将债务货币化,就不存在债务无法清偿的问题。然而,由于美元储备资产供给依靠美国政府债务发行,而偿债能力又取决于美元资产的价值,债务与资产质量之间的矛盾,形成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美元悖论。新冠疫情暴发更是强化了这一悖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比,美债市场投资者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外国持有的比例在明显下降。截至2021年中期,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美债总发行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过去多年的水平,更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形成巨大的反差(图2)。二是美联储量宽政策以购买国债实施,这使得美联储成为美债的最大买家。从效果看,美联储大规模的购债有效填补了美债需求缺口。但是,美联储资产购买实际上是从私人部门手中拿走政府债券以及证券化信贷产品中具有安全性质类别的资产,并没有减轻美国政府负债。外国人减少美债持有,增加对其他主权债的配置,这是出于储备资产多元化的需要,也反映了对美债可持续性存在着担忧。外国人持有美元资产是对美元地位的最大支撑,一旦出现某种疑虑,其对储备资产配置的效应具有全球性。
美元的上述收益和成本并存的现实,也反映在美元强势或弱势的历史观察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经历了大幅度升值。到1985年美元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升至150的历史高点。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等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时期。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七国集团于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承诺通过汇率调整和货币政策协调促使日元和马克等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合作努力十分奏效,美元随后大幅度贬值,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也有所缩小。直到1987年,七国集团再度联手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旨在阻止美元过度贬值。然而美元低迷势头未改,到1995年美元有效汇率已调至101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美元作为官方外汇储备比重也从前期的85%下滑至60%左右。面对贬值压力,新上任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一改历任财长不谈汇率的传统,第一次挑明对美元贬值的担心,明确说“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希望美联储和其他央行联合干预支持美元。
鉴于美元的特殊性,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享受美元储备地位带来的收益与其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美国采取对美元汇率“善意忽视”的态度,这是因为强势美元是美元储备地位的综合体现,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所带来的成本,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更加关注贸易平衡,相信弱势美元有助于增加美国出口。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向美联储施压,希望压低美元币值。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元因避险需求和美国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而经历了升值过程,同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在扩大。美元升值有助于美国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入,有助于巩固美元储备地位,但无助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元市场的国际影响力,美国政府意愿的变化对美元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会通过国际市场进一步得以放大:“如果美国的变化显示对美元国际角色的疑惑,那么国外的变化将加深这一疑惑”(Eichengreen, 2011)。
无论哪一种货币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都不可避免在享有特权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负担。这其中所形成的种种悖论,在单一货币成为主导储备货币的体系中会有所放大。
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储备体系需要处理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要素:国际储备需求、储备货币的供给和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特里芬难题阐释了这一矛盾:在美元-黄金本位下,国际储备需求增加客观上需要发行国提供储备货币的供给,而当供给增加到超出了储备货币所能提供的清偿力,则储备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受到动摇。而后者又会动摇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看似简单的逻辑,实则深藏一无解的问题。这是因为,即便在浮动汇率下,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的两个非对称性,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也同样存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对储备货币需求要大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储备货币供给;二是发达国家的信用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这两个非对称实际上从财政角度和公共债务角度阐述储备货币的清偿力难题(Obstfeld,2011)。
国际储备货币的清偿力问题以及供求矛盾仍将困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良性运转。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或许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储备资产的供给,比如增加欧元和人民币等法定货币的储备资产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打破主导货币的TINA效应,分担储备货币所承担的成本,尽管这一多元化进程很可能十分漫长。
(本文终稿“美元储备地位的深层次矛盾”刊载于《中国金融》2022年第4期。)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北京五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